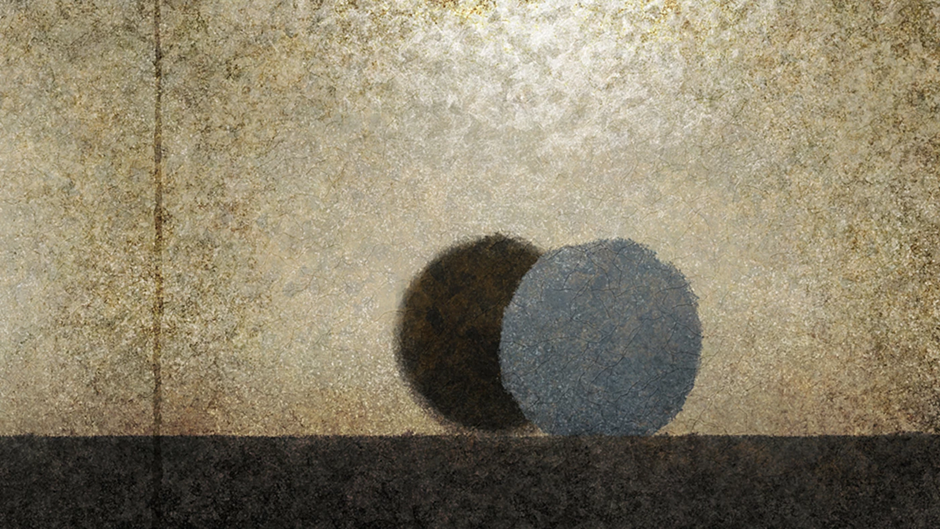
任何遇到反基督教论战的人都会很快遇到这样的指责:基督徒在全球范围内所庆祝的一个主要节日——复活节——实际上是从异教徒的节庆活动中借用或篡改过来的。 我经常在穆斯林口中听到这种想法,他们声称后来的基督徒与异教妥协,淡化了耶稣的原始信仰。
这种说法主要是基于英语和德语的庆祝活动 名称(英语为 Easter,德语为 Ostern)与异教的联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其他欧洲语言中,基督教庆祝活动的名称来自希腊语的 Pascha,而它又来自希伯来语的 Pesach,即逾越节。 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逾越节。
当然,即使基督徒真的参与了 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用当地人的语言或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信息和敬拜,这也绝不意味着 教义上 的妥协。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试图将基督救赎融入当地文化,同时清除与《圣经》规范相反的做法。 毕竟,基督徒说的是“受难日”(Good Friday),但他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纪念对北欧/日耳曼神后 芙蕾雅(Freya)的崇拜。
事实上,就复活节而言,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纪念以及它的名字都不是来自异教。
一个有着古老根基的庆祝活动
关于复活节的异教起源,通常的说法是基于圣比德(Venerable Bede)(673-735)的评论,他是一位英国修道士,撰写了英国第一部基督教历史,是我们了解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 《论时间的计算》(De temporum ratione,约730年)中,比德这样写道:
在古代,英国人根据月球的运行轨迹来计算他们的月份——如果我只谈论其他国家的年份,却对自己国家的年份保持沉默,这似乎不合适。 因此,按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方式,月份的名称来自于月亮,因为月亮被称为 mona,月份被称为 monath。 被拉丁人称之为一月的第一个月,就是Giuli;二月被称为Solmonath;三月是Hrethmonath;四月是Eosturmonath ... Eosturmonath的名字现在被翻译为“受难月”(Paschal month). 以前,这个月份以前是以他们的一位名叫Eostre的女神命名的。为了纪念她,人们在该月举行了宴会。 现在,他们用她的名字来称呼那个受难节,用古老传统中用来已久的旧名称来称呼新仪式的快乐。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实际的复活节 庆祝活动 是否来自于异教徒的节日。 这很容易回答。 北欧/日耳曼民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对来说是基督教的后来者。 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I)于596/7年派出由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领导的传教士团体,前往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 772年,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治下,欧洲的撒克逊人开始被强行皈依基督教。 因此,如果“复活节(Easter)”(即基督教的逾越节庆)是在这些日期 之前 就已庆祝的,那么任何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的“Eostre”异教节日对此事就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上,有明确的证据显明,基督徒在第二世纪就已经庆祝了复活节/逾越节,也可能更早。 由此可见,起源于地中海流域的基督教复活节/逾越节庆祝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日耳曼异教节日的影响。
名字代表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复活节(Easter)”这个节日的 名称 是否来自基督教庆祝活动被混淆于英格兰和日耳曼文化中对一个据称是异教徒生育女神“Eostre”的崇拜。 比德的这段话有几个问题。 罗纳德·哈顿(Ronald Hutton)教授(英国异教和神秘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在他的《太阳站》(The Stations of the Sun)一书中批评了比德对其他异教节日的粗略了解,并认为关于Eostre的说法也是如此:“它属于贝德承认只是他自己的解释的那一类,而不是普遍认同或证明的事实。”
这让我们看到了下一个问题:除比德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位盎格鲁—撒克逊女神的存在。 在北欧古文献(Norse Eddas)或欧洲大陆的古代日耳曼异教中都没有相应的女神。 因此,哈顿建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Estor-monath 只是指‘开放的月份’或‘开始的月份’,”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不列颠群岛在三月或四月有一个前基督教节日。
对于 Eosturmonath 与异教女神有任何关系的说法,还有一个反对意见。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日子通常以神的名字命名,如星期三(“Woden's day”),而他们的月份名称要么是日历性的,如 Giuli,意思是“轮子”,指的是年轮;要么是气象—环境性的,如 Solmónath(大约是二月),意思是 “泥月”;要么是指该时期的行动,如 Blótmónath(大约是十一月),意思是屠宰动物时的“血月”。 除了(按比德的说法)Hrethmonath(大约是三月)之外,没有其他月份是专门为一个神灵而设的。据他声称,这个月份是以女神 Hrethe 的名字命名的。 但与 Eostre 一样,没有其他关于 Hrethe 的证据,也没有在日耳曼/北欧神话中的任何对应物。
就比德给出的解释,另一个问题涉及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 查理曼大帝的廷臣和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约775-840年)告诉我们,查理曼大帝的改革之一是重新命名月份。 四月被重新命名为 Ostarmanoth。 查理曼大帝说的是日耳曼方言,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一种,尽管他们的具体白话是不同的。 但是,查理曼大帝为什么要把古罗马人对春季这个月的称呼改为 Ostarmanoth 呢? 查理曼大帝是打击日耳曼异教的。 772年,他袭击了异教的撒克逊人,并砍倒了他们的大立柱 Irminsul(以他们的神Irmin命名)。 他强行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并在他们因此而造反时野蛮地镇压他们。 因此,查理曼大帝似乎不太可能以一个日耳曼女神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月份。
春天的假日
那么,为什么讲英语的基督徒把他们的节日称为“Easter”呢?
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拉丁语中的 in albis(“穿白袍”)一词,本为基督徒指称复活节时所用,后来进入了古德语(Old High German),变成 eostarum,就是“黎明”。 尽管日耳曼人生活在罗马帝国之外——尤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与罗马帝国相距甚远,但仍有一些证据表明早期日耳曼人借用了拉丁语。 这一理论假定,该词是在引入罗马影响或基督教信仰后才开始流行的,而这一点是不确定的。 但如果准确的话,这将证明这个节日不是以异教女神命名的。
另外,正如哈顿所建议的,Eosturmonath 只是意味着“开放的月份”,这与拉丁语中“四月”的意思相当。 撒克逊月和拉丁月(在历法上相似)的名称都与春天有关,春天是花蕾开放的季节。
所以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地区的基督徒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的逾越节——起初无疑是口语化的——只是因为它发生在 Eosturmonath/ Ostarmanoth 前后。 用当代的例子做类比,比如美国人有时将12月这段时间为“节日”,是与圣诞节和光明节有关,或者,当人们有时说“圣诞节前后”发生的某些事情时,通常是要说事情发生在年关的时候。 那么,基督教的“Easter”这个称呼基本上反映了它在日历中的一段日期,而不是复活节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一个所谓的异教神灵。
当然,基督教对复活节的纪念不在于庆祝活动的 名称,而在于其内容,即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纪念。 正是基督对罪、死亡和撒旦的征服,使我们有权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安东尼·麦克罗伊(Anthony McRoy)是英国中东研究协会的研究员,也是英国威尔士福音神学院的伊斯兰研究讲师。
翻译:Pearlyn Koh
责任编辑:吴京宁

Annual & Monthly subscriptions available.
- Print & Digital Issues of CT magazine
- Complete access to every article on ChristianityToday.com
- Unlimited access to 65+ years of CT’s online archives
- Member-only special issues
- Learn more
Read These Next
- Trending
 While we pray for peace, we need moral clarity about this war.
While we pray for peace, we need moral clarity about this war. - From the Magazine
 We’ve got little information on Jesus’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But that’s the way God designed it.españolFrançais
We’ve got little information on Jesus’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But that’s the way God designed it.españolFrançais - Editor's Pick
 Beyoncé’s right. Whether listening to Cowboy Carter or reading theology, diversity is a good thing.
Beyoncé’s right. Whether listening to Cowboy Carter or reading theology, diversity is a good thing.













